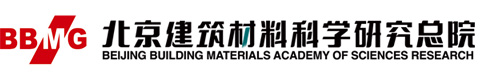
HTH捕鱼: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,用来安放疲惫的灵魂。当都市的钢筋水泥让人喘不过气,远方的海浪声就成了最温柔的召唤。
许多人倾尽所有,只为奔赴一场关于诗和远方的梦想,他们以为那是新生活的开始,却不知命运的馈赠,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
生活就像一个朴实的农民,你种下什么,它最终就会让你收获什么,一分不多,一分不少。
北京的秋天,天高云淡,可林启和苏晚却觉得那片天空离自己很远,远得像另一个世界。林启,三十五岁,在一家互联网大厂里像一颗螺丝钉,拧了十年。每天早上,他被闹钟从浅得像层薄冰的睡眠中惊醒,脖子像生了锈的零件,发出“咯吱”的响声。他看着镜子里发际线又后退一毫米的自己,感觉生命的热情正随着那些代码,一行行地被消耗殆尽。
苏晚比他小两岁,是个自由插画师。听起来很美,可只有她自己明白,自由的代价是无休止地迎合甲方的奇思妙想。她画的风景越来越美,可她已经很久没有亲眼看过真正的风景了。两人在北京的这片人海里沉浮,手里攥着辛苦攒下的二百五十万,这一个数字在北京的房价地图上,连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都点不亮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普通的夜晚。苏晚像往常一样浏览着网页,寻找插画的灵感,一张照片丝毫没有征兆地跳了出来。照片里,一栋白色的二层小楼静静地立在海边,蓝色的百叶窗像含羞的眼睛,门前是一个看起来有些荒芜但潜力巨大的花园。标题写着:南方海滨小镇“浅湾”,独栋别墅,带花园,急售,二百万。
林启凑过去,起初不以为意,可当他看到苏晚眼中那团重新燃起的火焰时,他的心被触动了。是啊,他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?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,这句被说滥了的话,此刻却像一道光,劈开了他们生活的阴霾。去看看,这个念头一旦生根,就疯狂地生长起来。
几天后,他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,来到了这个叫“浅湾”的小镇。接待他们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叫小王,皮肤被海风吹得黝黑,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。他骑着一辆旧摩托车,载着他们穿过镇上狭窄但干净的街道,空气里满是海盐和鱼腥的混合味道,不难闻,反而有种踏实的生活气息。
别墅比照片上看起来还要好,只是因为长时间没人住,显得有些萧索。墙皮有几处剥落,花园里的杂草长得快有半人高。林启绕着房子走了一圈,他是个理性的人,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问题。比如二楼的窗框有些变形,墙角有淡淡的水渍。
“嗨,林哥,你不知道,”小王挠了挠头,熟络地称呼着,“原房主是一对夫妻,急着移民去国外,手续办得急,所以才低价抛售。产权什么的绝对清晰,你们放心。”他又补充了一句:“就是走得急,家里有些旧东西都没有来得及搬走,后来委托我们给处理了。”
苏晚已经完全被迷住了。她站在二楼的阳台上,闭上眼睛,仿佛能听到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,能闻到花园里花开的香气。她想象着自己在这里支起画架,林启在楼下侍弄他的花草,那样的生活,光是想想就让她心醉。
看着妻子眼里的光,再想想北京那间永远晒不到太阳的出租屋,林启心里的那点疑虑被巨大的向往压了下去。二百万,买一个全新的开始,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未来,值了。
合同签得很顺利。拿到钥匙的那一刻,林启和苏晚觉得他们握住的是后半生的幸福。他们辞掉了工作,告别了北京的朋友,像两只迁徙的候鸟,飞向了南方这片温暖的海岸。
接下来的两个月,是他们结婚以来最快乐、最充实的一段时光。林启这个过去的“码农”,此刻展现出了惊人的动手能力。他修补墙壁,更换老化的电线,给木质的门廊刷上新的防水漆,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,可他脸上的笑容却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灿烂。
苏晚则成了这个家的总设计师。她跑遍了镇上和邻市的家居市场,淘来了各种带着海洋气息的装饰品。窗帘换成了天蓝色,沙发上摆着海星形状的抱枕,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帆船。
花园的改造是工程量最大的部分。他们拔掉杂草,翻松了土地,重新铺上草坪。在清理花园西北角那棵老榕树下的时候,林启的铁锹碰到了一块硬物。他拨开泥土,发现是一块铺设得不太平整的石板,石板中央有些微的下陷。
他们没太在意,把石板周围清洗整理干净,苏晚还从镇上买来一个沉重的陶制大花盆,正好摆在石板上,里面种上了她最喜欢的三角梅。
他们的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渔民,姓张,人们都叫他老张。老张天天都会沉默地挑着渔具从他们家门口路过。看到这对年轻夫妻热火朝天地改造着院子,他只是点点头,那张被海风刻满皱纹的脸上,眼神总是很复杂,像同情,又像是惋惜。苏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,他只是“嗯”一声,从不多话。
两个月后,别墅焕然一新。傍晚时分,夫妻俩最喜欢做的事,就是搬两把藤椅坐在门廊下,开两瓶冰啤酒,听着不远处的海浪声,看着天边的晚霞。过去十年在北京的奔波和劳累,似乎都在这咸咸的海风中消散了。他们都觉得,这才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,一个美好的、崭新的人生,就此展开。
日子像浅湾的海水,涨潮又退潮,平静地流淌了半年。最初的新鲜感和激情,被日常的琐碎慢慢冲淡。田园诗般的生活,也露出了它现实的一面。小镇的医疗条件不好,一次林启感冒发烧,跑了几个小诊所都看不好,最后还是开车去邻市的大医院才挂上水。苏晚想给未来的孩子找个好点的幼儿园,发现镇上唯一的选择,条件还不如北京的普通社区幼儿园。这些事情,让他们偶尔会怀念起大城市的便利。
苏晚的创作也遇到了瓶颈。每天面对着同样的海景,再美的景色也变得单调,灵感像退潮后的海水,迟迟不肯回来。林启尝试着在网上接一些编程的私活,但收入很不稳定,家里的积蓄在一点点消耗。他们开始为了一些小事争吵,比如晚饭吃什么,比如今天谁该去镇上买东西。这些在北京时可忽略不计的摩擦,在这栋安静的别墅里,被无限放大。
一些奇怪的事情也悄悄发生了。苏晚不止一次对林启说,她晚上睡觉时,总感觉能听到一阵阵若有若无的哭泣声,很轻,很压抑。林启起初以为是海风吹过窗棂的声音,安慰她不要胡思乱想。可苏晚坚持说那声音是从房子内部传来的。
一个周末的下午,林启打扫阁楼。那是一个很久没人进去过的空间,积满了灰尘。在一个角落里,他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旧木箱。箱子没有上锁,他吹开上面的灰,打开了它。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,而是一沓画纸。
画的作者应该是个小女孩,笔触天真烂漫。最开始的几张,画的是蓝色的大海,金色的沙滩,还有在花园里荡秋千的小女孩,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。林启翻着翻着,心头却慢慢沉了下去。画到后面,画风陡然一变。天空变成了灰色,大海是黑色的,那个小女孩不再笑了,她被画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,窗外是狰狞的树影。最后几张画,已无任何具象的形态,只是用黑色的蜡笔在纸上疯狂地涂鸦,那些杂乱的线条里,仿佛藏着无尽的痛苦和绝望。
林启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从脊背升起。他默默地合上箱子,把它推回了角落。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苏晚,妻子的情绪已经够敏感了,他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。这个小小的秘密,像一根看不见的刺,扎在了他心里。
夏末,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台风“海燕”正面登陆了这片沿海地区。狂风像愤怒的野兽,在窗外咆哮了一天一夜。暴雨如注,整个浅湾镇都泡在水里,仿佛要被大海重新吞没。林启和苏晚躲在别墅里,听着风雨拍打门窗的声音,心惊胆战。他们别墅的院墙,在暴雨的冲刷下,塌了一小段。
两天后,风雨终于停了。天空像被洗过一样,蓝得刺眼。林启和苏晚迫不及待地走出房门,查看损失。院子里一片狼藉,到处是断掉的树枝和吹落的瓦片。就在这时,一股奇怪的味道钻进了他们的鼻子。
那是一种他们从未闻过的味道,混杂着海产品的腐烂腥气,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、像是化学药品的甜腻气味,闻久了让人头晕恶心。
“什么味儿啊?不会是死了什么大老鼠吧?”林启捂着鼻子,皱着眉头在院子里四处寻找。
“不像……这味道太怪了。”苏晚的脸色有些发白,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关于老房子的恐怖故事,还有林启在阁楼里发现的那些压抑的画。
他们循着气味的来源,一步步地走,最终停在了花园西北角,那棵老榕树下。之前被他们用来压住石板的那个大陶制花盆,已经被台风吹倒,摔得粉碎。而那块原本就有些下陷的石板,在暴雨的猛烈冲刷下,周围的泥土被水流带走,整个石板下陷得更厉害了,几乎塌下去一半。那股令人作呕的异味,正是从石板的缝隙中,丝丝缕缕地冒出来。
接下来的几天,对林启和苏晚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。那股异味非但没有因天气放晴而消散,反而在太阳的暴晒下,愈发浓烈。整个院子都弥漫着这股怪味,他们连窗户都不敢开。他们试过用土重新把缝隙掩埋,也试过用消毒水浇灌,可都无济于事。这股味道像一个看不见的幽灵,缠绕着他们,折磨着他们的神经。
这天下午,邻居老张挑着渔具,又一次从他们家门口路过。他看到林启正拿着铁锹,徒劳地往石板上堆土,便停下了脚步。他浑浊的眼睛看了一眼那个角落,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“那地方……最好别动。”老张沙哑着嗓子说,“前一家人走的时候,就嘱咐过。”
老张的话像一把锤子,重重地敲在了林启和苏晚的心上。前房主嘱咐过?他们隐瞒了什么?为啥不让动那个地方?移民的谎言背后,到底藏着怎样一个秘密?恐惧和猜疑像藤蔓一样,在他们心里疯狂滋长。
林启的理性告诉他,最正确的做法是报警。可苏晚却死死拉住了他。这栋别墅是他们全部的家当,是他们逃离过去、奔赴未来的全部希望。万一……万一挖出什么不祥的东西,这房子就彻底毁了,他们的生活也会被彻底摧毁。
夜里,苏晚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,她说她又听到了哭声,这一次特别清晰,好像就在床边。林启抱着瑟瑟发抖的妻子,一夜无眠。他知道,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这股味道,这个秘密,就像一个正在溃烂的伤口,再不处理,他们两个人的精神都会先被拖垮。
在持续的异味折磨和内心的巨大恐惧、好奇驱使下,林启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不管下面是什么,他必须亲手把它挖出来,把谜底揭开。
那是一个格外闷热的下午,空气粘稠得像化不开的糖浆。林启从储藏室里找出了铁锹和一根撬棍,他的手心因为紧张而渗出了汗。苏晚脸色苍白地站在一旁,嘴唇紧紧地抿着,像一尊紧张的雕像。
林启将撬棍石板的缝隙,深吸一口气,用力向上一抬。石板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沉重,很轻易地就被撬开了。就在石板被移开的一瞬间,一股比之前浓烈百倍的恶臭扑面而来,那股混合着腐烂和化学药剂的味道,熏得两人连连后退,捂着嘴干呕起来。
石板下面,是一个大约一米见方的土坑,里面的泥土是松软的,明显是后来回填的。林启强忍着不适,戴上厚厚的劳工手套和口罩,拿起铁锹,开始往下挖。
泥土很湿润,挖开表层后,他发现下面混杂着许多白色的粉末状物质。他捻起一点,放在鼻子下闻了闻,是一股刺鼻的石灰味。这是生石灰,通常用来防腐和掩盖气味。看到这些,林启的心沉得更厉害了。
一铲,两铲……每一铲土被挖出,夫妻俩的心就跟着揪紧一分。苏晚紧张得几乎没办法呼吸,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,指甲深深地嵌进了肉里。她不敢看,又忍不住不看,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越来越深的土坑。
挖了大概有半米深,铁锹的尖端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,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闷响。不是石头,那种触感带着一丝韧性。林启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。他扔掉铁锹,蹲下身,用手小心翼翼地拨开周围的泥土。
一个用厚厚的黑色防水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箱子轮廓,慢慢显现出来。箱子不大,看起来像一个手提的行李箱大小。上面还用粗大的透明胶带一圈一圈地缠绕着,密封得极其严密。
林启和苏晚合力将这个沉甸甸的箱子从土坑里抬了出来。一种巨大的、不祥的预感像乌云一样笼罩了他们。这一定不是什么金银财宝,谁会用这样的形式埋藏财宝?
林启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。他看了一眼身边的苏晚,妻子的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,脸上满是恐惧。
“已经到这一步了。”林启咬着牙,声音有些嘶哑。他知道,现在停下来,这个箱子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梦魇。他必须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。
他从工具箱里找来一把锋利的美工刀,蹲下身,开始一层一层地割开外面包裹的胶带和油布。油布被割开后,露出来的是一个深蓝色的箱子。林启认得出来,那是一个儿童专用的医疗保温箱,通常用来运送需要低温保存的药品或者标本。箱子的一角还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,但上面的字迹因为受潮,已经模糊不清了。
看到这个医疗箱,林启的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。所有的猜测都指向了一个最坏、最恐怖的方向。他抬头看着苏晚,艰难地说道:“你……你回屋里去吧。”
林启不再劝她。他找到了保温箱的金属卡扣,那卡扣有些生锈了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,深吸一口气,猛地将卡扣扳开。



